月照前墀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雾添花cdij.cn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“难为他还记得春雨。”
只是不知他特地来寻春雨,实际上究竟打着何等的算盘。
张月盈的眉毛紧紧皱了起来,她搁了楚太夫人让小厨房特意给她备的牛乳茶在一旁,吩咐春燕:“就让他去正堂等着,我得空了自会见他。”说完,她又跟楚太夫人品起了玉颜斋新研制但还未发售的唇脂。新唇脂按所放色粉的比例不同,调和成了不同的色号,用了诗词名句来取名。最合张月盈心意的是一款日出江花,是前世一度流行的山楂红,非常衬肤色。楚太夫人看了只叹:“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,也同你一般喜欢这样鲜亮的颜色。”随手选了一款朝日长,粉色偏紫,很素雅的颜色。张月盈又让春燕端来了妆盒,拿起妆笔在楚太夫人脸上涂涂画画,楚太夫人一如往昔任孙女施为。
另一边,张怀仁被晾在了正堂,一边喝茶一边打量着山海居里的布置。大到墙壁上的四幅贴金花笺、多宝阁上的釉彩百花景泰蓝大瓷瓶,小到他于中的天青色汝窑裂冰纹茶蛊,都叫他移不开眼暗自估
算着其中价值。
张怀仁是庶长子,并不招小冯氏待见,薛小娘在世时,他被拘在院子里,没几年又被打发出京没见过楚太夫人几面,印象里的张月盈也只是一个吃奶的小娃娃。他的消息并不算灵通,也就回府这几日从
下人口中窥得这位王妃妹妹的脾性,张月芬惹出的麻烦,让她去顶锅她还真去了,应当不是个难拿捏的主。
等到接近午时,连换了三盏茶,张怀仁方听见正堂外边传来了稀稀拉拉的脚步声。门口的珠帘撩起一角,张月盈缓步入内,坐在了上首的位置,
她亦是头一回见这位大哥哥,因春雨的缘故对他事先存了不好的印象,故意晾了一晾他,让上茶侍奉的丫鬟悄悄观察了他的行止,对他的性格大体有了谱。她目光淡淡扫过张怀仁。比之张怀瑾,张怀仁长相更加俏似长兴伯。颧骨高耸,两颊从两侧削下去,鼻梁却挺得笔直,眼窝凹陷,那双眼睛里偶尔闪烁着野心的渴望。
与长兴伯一般无二。
张月盈客气道:“大哥哥到京数日,我都未曾知晓,实在是怠慢了。”
“卑不动尊,我岂敢劳王妃垂询,还是我来拜见更为妥当。”张怀仁起身,朝上首捐过一礼,礼仪不比京城的公子哥们差,显然下了一番苦功。
他姿态做得很足,张月盈却不以为意,开门见山说道:“明人不讲暗话,我与大哥哥并不熟稔,你特地跑来,当是有所求,我不习惯跟人弯弯绕绕大半天,就直说吧。”张月盈拿住了姿态,张怀仁瞬觉她与事先设想的大不一样,秉着以不变应万变的打算,道:“当初无意间给王妃添了许多麻烦,我为道歉而来。”果然还是话说一半留一半,跟打哑迷一样。张月盈阴阳怪气:“大哥哥久在通州,与我素不相见,如何给我添得了什么麻烦?”
“是春雨。”张怀仁只能道,“她也是顾念与我的情义,才帮忙传了消息,被人借题发挥,差点儿带累了王妃的清誉,是我的不是。只是听间吞雨被交由了您处置,想冒昧间问一下她的下落。”
终于进入正题了。
“你找她何事?”
“不怕王妃笑话,昔年我在伯府内处境尴尬,下人也都不把我放在眼里,饥一顿饱一顿的,多亏了她这个小丫蓝时时记挂着我,肯替我办事。当年我曾经许诺过她,如今中了举,也算有那么几分能为,
也到了该应诺的时候了。”张怀仁说得情真意切,叫外人听去了还觉得他分外知恩图报,成了举人老爷,还记得当您帮过他的一个小丫鬃。
听在张月盈耳中,只觉十分讽刺,暗嗤若不是被亲娘拿了刀子架在脖子上成胁,以春雨的心气,会跟他私下有往来?如今春雨脱籍成了良人,在玉颜斋当掌柜当得风生水起,他却又找上门来了。张月盈没了好气:“我听你称呼春雨一个小丫量,你心里大约便是如此看她的?别以为我不知晓,你正正当当该叫她一声表妹的。论情义也当论亲戚情义,而不是主仆情义。”
她言辞犀利起来,直击张怀仁痛处,他深恨的便是自己的出身,生母仅是府中的奴婢,别说小冯氏了,连木小娘和周小娘都比不了。
"王妃何苦如此挖苦我?"张怀仁强忍着没有垮脸。
“实话而已。春雨已被放良,从此天高海阔,任她来去自由,她在何处,我也无权过问。”张月盈语气漫不经心,一个眼色示意杜鹃,“来人,送客吧。”
“大公子请。”杜鹃闻言收了张怀仁的茶盏,请他出门。
“多谢王妃指点了。”张怀仁忿忿哼了几声,拂袖离开。
“姑娘。”眼见张怀仁走远,杜鹃凑到张月盈身侧,语气担忧。
张月盈盯着张怀仁的背影,道:“他大约之前有什么把柄落在春雨手上了,必不会就此善罢甘休,让人去跟春雨说一声,也好有个防备。”
“是。”杜鹃应声出了门。
会了会张怀仁,张月盈回了里屋,同楚太夫人一起用过了午饭,沈鸿影便亲自来了山海居,接了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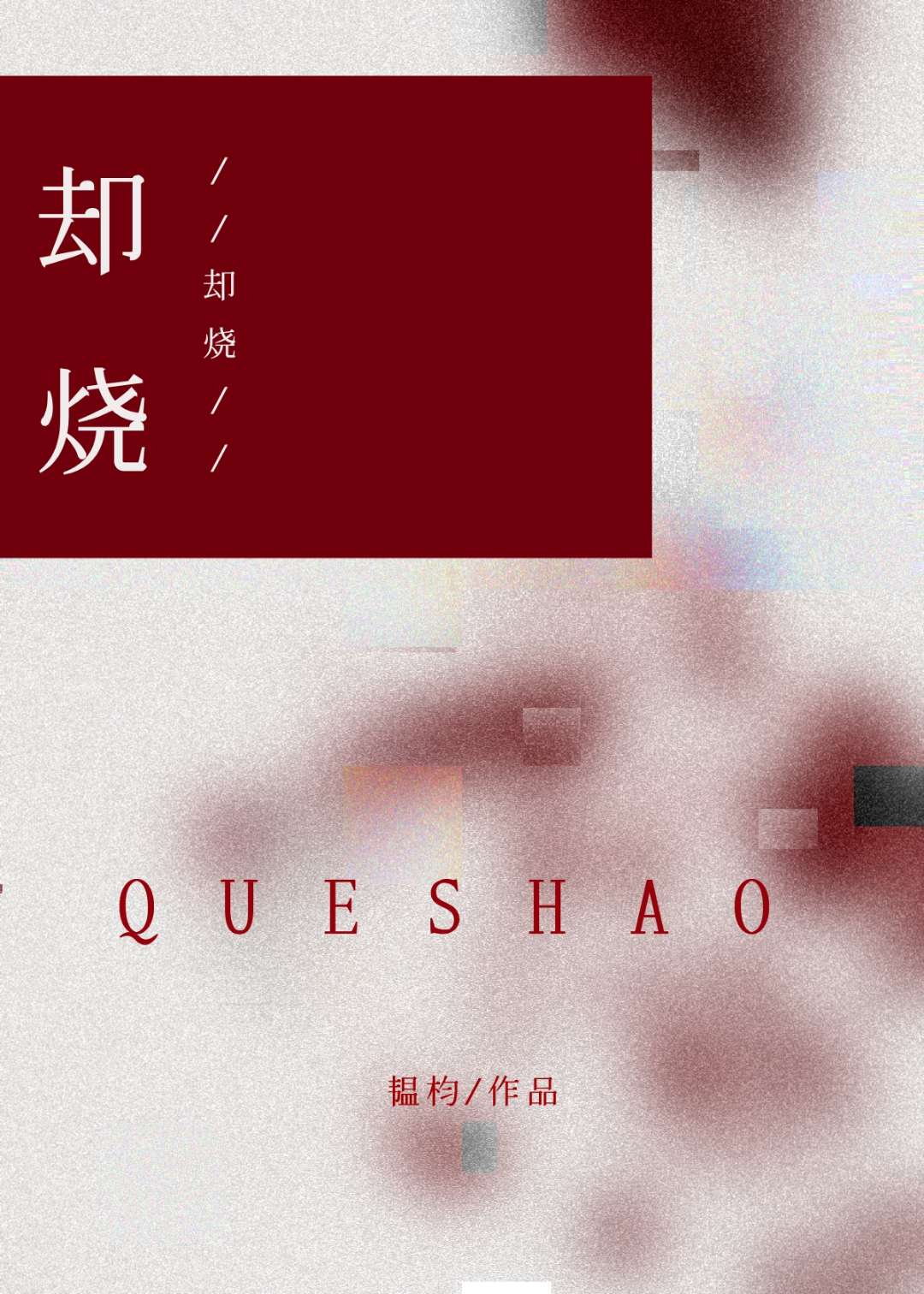


![[综英美]哥谭魔女](http://cdij.cn/images/61/d6666b1406df141714530e8fb5a45d82.jpg)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