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颗糖粒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雾添花cdij.cn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问我的行踪?”
姜颂宁也不和她打哑谜了,孟安澜忌日对亲人而言至关紧要,但薛亭洲未必记得清楚,她默了默,心平气和地开口。
“明日是亡夫忌日,若薛大人得空,可拨冗过来略坐片刻。”
“亡夫?”薛亭洲一字一顿,像在品味着两个字的意味,笑意不达眼底,“孟安澜什么身份,我又算夫人的什么人?非亲非友,我就不打扰了。”
如此这般,薛亭洲应该不会和孟老夫人一行人遇上了。
姜颂宁已然心安,正欲告辞,薛亭洲续道,“明日不便再见,请夫人移步,我还有话要说。”
薛亭洲坦然自若,姜颂宁不好忸怩,不然显得她心里有鬼似的。
给挽香吩咐两句,便随薛亭洲入了院落。
姜颂宁见过大大小小许多官吏,薛亭洲正派可靠,风姿鲜有人能与之相比。
她走在他身后,感觉自己像他手下管事小吏,在他的威势下不敢擅动。
一进门,景明连茶水都没给她倒,便快步走出掩上房门。
姜颂宁不解,这就是他的待客之道?
虽然也不是什么贵客,但一口清茶还是该给她的。
不然显得她很没有面子。
薛亭洲宽袖一挥,坐在交椅中,有些不耐地揉了下眉骨。
姜颂宁呼吸一滞。
发现自己过分紧张,暗自苦笑。
他神色不动,尚且有多少官吏在他面前大气不敢出。此时流露出不大愉快的情绪,她紧张一些也不奇怪。
若他府中有女眷,她就能和人坐下说话了,而不是和他面对面地交谈。
这个念头从脑中一闪而过,姜颂宁目光微动,发现他悄无声息地在打量她。
薛亭洲的审视并不下流,但压迫十足。
她轻吸了一口气,努力放松下来。
“你一定在想,我为何找你过来。”薛亭洲淡声道,“那日闯入厢房的男人,挽香应该告诉过你他的身份,但孟夫人好像一点也不意外,之后再无动作。”
王韬几无长处,但油嘴滑舌,会讨陛下欢心,无论是先帝还是今上,都对他多有关照。
姜颂宁知道王韬对她早有企图,过后回想起来当日之事,稍微一想就明白了。
王韬再是贪欢,也不会在宁远侯府的地盘上干出这等事,对她下手的只会是顾家人。
姜家和顾家早有旧仇,但胳膊拧不过大腿,再是愤懑不满,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反击。
二伯和父亲走后,姜家没有能支撑门庭的男子,姜识和更小的几个晚辈,还未长成。
静候时机是姜家唯一的选择。
姜颂宁面对薛亭洲的诘问,神色未改,轻笑道:“我人微言轻,至多不痛不痒地报复回去。若下了狠手,得逞不难,之后又怎能善了呢。”
“薛大人心里明白,为何又来问我。”
薛亭洲指尖在小几上轻点两下,“你选了孟安澜,投靠孟家。但他们并不能护你周全。”
话题绕回到这上头来,姜颂宁怔了怔,垂眸道:“我的选择全凭心意,当时的选择,自然是当年审时度势过后的决断。我并不后悔。”
“孟夫人如今学会了忍让。”
薛亭洲走到她面前停下,“但你有没有想过,如今还有另一种活法。这口气,未必只能忍下去。”
姜颂宁若是孤身一人,做事自然能随心所欲。
但有看重的亲人在她身后,她没有随便下赌注的胆气。
薛亭洲说的这些,她不是不心动,但现在手里没有他看得上的筹码。
薛亭洲不会做亏本的买卖,她又要用什么来换?
孟家不会看在她的面上为姜家冒险。
再等几年,竣工之时便能洗脱二伯与父亲的污名。
但幕后主使,不会无凭无故因着这点陈年旧事倒台。朝中无人造势,秀禾县喜讯传来,根本不会有人主动翻出这多年前的旧案。
姜颂宁定了定神,攥紧手心,抬眸看他:“薛大人想要什么?”
薛亭洲捏住她的指尖,往她的掌心摩挲,将她的手纳入掌中,感受到她身子慢慢变得僵硬,他有种得逞的痛快。
是了。他早该用这种手段。
姜颂宁看着交握的手,深吸一口气,颤声道:“你这是何意?”
“男欢女爱,人之常情。夫人年轻貌美,我见之心动。”薛亭洲刻意停顿下来,默了两息,“夫人药效未退,倘若孤枕难眠,还有比我更好的选择吗?”
看她回不过神,难以接受的模样,薛亭洲不轻不重地捏了捏她的手指,轻笑道:“明日是孟安澜忌日又如何。逝去四年整,又不是尸骨未寒。”
姜颂宁怔忪不语,没想到薛亭洲竟然是这般想法。
听人墙角传入耳中的污言秽语固然露骨,但都不及他此时所言。
姜颂宁咬了咬唇:“若想羞辱戏弄于我,你大可选别的法子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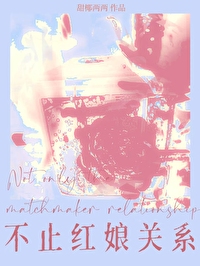


![清冷美人她不按剧本来[快穿]](http://cdij.cn/images/1290/9e2f51fbc72837db04ae96de093f4153.jpg)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