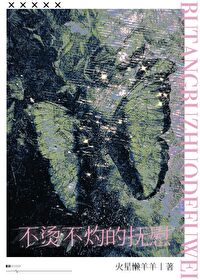阿森AHSEN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雾添花cdij.cn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,沈丽予也醒了,问道:“母亲?”她伸手放在母亲的额前。还是烫。
“下过雨?”林丽问女儿。她的嗓音嘶哑得厉害,每吐出一个字,好似就会撕开她的喉管。
这时,陈师傅从洞外走进来了。借着一点月光,林丽见他递过来一片卷起像茶杯一样的树叶,里面装着一点点清水,于是接过喝下了。
沈丽予从母亲身边起来,从怀里拿出阿成送的饼,对陈师傅道:“劳烦您照看母亲,吃些干粮吧,我再去取些露水。”
林丽想喊住女儿,让她别去了,却不怎么喊得出声,固执地把手悬在半空。
陈师傅按下林丽的手,道:“让三娘子去吧。就让她做些事,就不会胡思乱想了。”他把绢帕里的饼撕开,一点点地喂给林丽吃,道:“孩子,吃吧,吃饱了病才会好。”
林丽觉得鼻子酸酸。可自己烧得久,没怎么喝水,眼泪都流不出来。她吃了点饼,喝了些丽予取回来的水,很快又昏睡过去。
逐渐地,陈师傅也撑不住了,开始咳嗽,发起了低热。
于是,沈丽予把母亲背在自己身上。
夜里的风很是寒凉,她将父亲的衣袍盖在母亲背上,长长的手袖绕到她的脖子下系紧系牢。
母亲在她的背上,有时醒了,和她说了些话就又睡了。
沈丽予忽地想起了以前,父亲出征去了,母亲也是这样把烧得说胡话的自己背在身上,在黑夜里跑出府,跑了几条街,找到郎中去治病。
她把脸转过去,贴着母亲发烫的脸颊,听着那微弱地呼出的热气。她是那样害怕,害怕自己转头时,就发现母亲就没了体温,没了气息。
陈师傅听见她的啜泣声,忍着不适,走上来问她,要不要换他背一段路。
沈丽予摇头,暂停脚步,掂了掂手,让母亲再往上些趴着,托起母亲的手握得更紧。
·
沈丽予就这样背着母亲,和同样生着病的陈师傅走走停停,已过去好几日。
雨停了又下。
烧退了又起。
只有水,没有干粮。
沈丽予将将母亲和陈师傅安顿在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下,开始走回头路。
走了一阵儿,她眼前就出现了来时路过的一个简陋的小茶摊。老板下巴上有一颗痣,身上穿着带补丁的衣袍,在这个几根棍子搭起来的棚子下,与妻子叫卖着便宜的茶水和馒头。
即便那些只是几个钱,沈丽予也拿不出来。她身上没有任何可以抵当的财物。她看着那些白花花的馒头,发觉自己其实早已经饿得头昏。
那小摊被许多走过远路、想要歇脚的乡民和商人围住,他们与摊主夫妻一样,在这山野中忙于维持生计,疲于奔波,只得在这片简单、温馨的空闲里苦中作乐。
他们都没有注意到,就在小摊不远处站着的沈丽予。
她就这样站在那里,根本挪不开脚。她盯着那堆馒头,完全挪不开眼。疲惫联动着复杂的思绪与情绪搅弄着她的自尊与思考。沈丽予突然对他们这样的闲憩生出了羡慕,甚至是妒忌。她根本不敢、更不能这样停下。
如果再没有吃的,她不知道生着病的母亲还能熬多久。对病患而言,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的馒头,也能生出一点恢复的力气。
周围滴滴答答的声音又响起了。这阴沉的天重新下起了绵绵小雨。
蒙蒙的雨水、热茶还有蒸笼冒出的热气混杂在一起,遮住了人的眼睛。
·
沈丽予出去了很久。
陈师傅有些担心了,准备把林丽背在身上,再出去找三娘子。可外面突然又下起了雨。林丽还在低热之中,不能再淋雨了。
正当他为难的时候,他的眼前却跑回来了头发湿哒哒的三娘子。她从怀里取出一个没有被淋湿的大馒头,手上还抓着一些青涩的果子。
沈丽予把馒头掰成两半,递给陈师傅一半。
陈师傅却只吃掉了果子,让沈丽予把馒头喂给林丽。他看着这孩子,把那块如同珍宝一样的馒头一点点地撕开,小心翼翼地全都喂进她母亲的嘴里。
三娘子没有钱,怎么拿到这样一个热气腾腾的馒头呢?
陈师傅不想问,一点都不想问。
·
须臾,雨雾中冲过去两匹马。
“啪嗒、啪嗒”的马蹄声渐渐地变响,又渐渐地变小,再是两声叠在一起的“吁”。
适才冲过去的两匹马,好像回了头,来到了沈丽予身后。
她把手里没吃完的半个青果扔掉,即刻从靴子里拔出了匕首,对准了这片白茫茫的雨雾中从马上下来的两个身形高大的人。
她和母亲已经被通缉了吗?
是那些把林家人抓走当成罪犯的官兵认出她们了吗?
沈丽予的心口扑扑地狂跳,呼吸变得急促,刀举得更高,人却在向后退。
是那两个人先开了口,边走边问道:“沈娘子吗?我们来找夫人和您的!”

![卡牌大师[末世]](http://cdij.cn/images/1284/d669636947b6007d228149ba5f97826b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