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分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雾添花cdij.cn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不得不承认,砂金十分好用。
温顺,聪慧,善解人意,观察细致,完美做到了我当时所说的懂事听话,百依百顺,种种表现也堪称为茨冈尼亚版本的田螺姑娘。
只要不是下雨天,空气每日会流通三次,在清晨、午后与傍晚。
前一日的衣物第二天会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橱柜。
餐桌上、床头、客厅中不重样的插花与绿色盆栽。
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还未伸手就被递上拐杖,一个眼神想要的东西就已经到跟前。我不必再思考一日三餐的食谱,何时洗衣何时晾干,或者其他一切琐碎杂事,只需要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写文稿,或是盯着窗户与木制地板边缘的飞扬尘土发呆。
这样下去似乎会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的,每当我想要委婉地告知他没有必要做到这个程度,撞入蓝紫色的玻璃瞳眸时,唇边的话语又不自觉地转弯。青年是比我高的,却总在仰视我,昂起的脸天真且无辜,如同一株柔软依赖的苇草。
躯体中的瘾症已然缓慢地消退,我没有再看到过他狼狈不堪的模样,他有时会离开短暂的时间,再一次出现时总是干净的,安静的,身上带着淡香,依稀能辨别出是石楠花与香薰交织的气味。
我有时会生出无法溶解的困惑,亲力亲为这些细小的琐事为何让人兴致勃勃,展露出这样心满意足的神情,再精妙的骗局也不至于做到这个地步,何况现在的我并没有价值。难道是因为与无边的残酷过去相比,这样贫瘠无趣的生活已经足够了吗?
也许,是足够的。
在某一日我无聊地翻阅着诗集,黄昏的柔光与风声透过窗户,一抬眼看到的人也是无所事事,托着下颌,嵌在了熹微涣散的光影中同样看向我。
他似乎不自觉地微笑,笑意弥散在言语间,在我开口前便轻声询问,需要什么吗,林。
我微微摇头,视线穿过了那寰宇中独特的环形瞳孔、分明的眉眼、随风浮动的金色发丝,他的额发边缘是人造梦境那般如幻的布景,是金红波浪似的漫天云层,是涂满橄榄色颜料的高空。
真是漂亮啊。
我这么想着,补充了一句:不用,不用。我只是在看晚霞。
.
这是一段足够平和的回忆。
平和到某位相识的焚化工闯入我的忆海,将它百倍速快进看完后,含笑着觑向我:“真没想到现在的你挺擅长养狗啊,丰饶的空壳。”
“你怎么会不知道?这不叫得很欢吗?”
我也看向她,微笑,“记忆的乞食狗。”
长生对于精神的折磨是久散不去的,因而我的应对措施是只会留下必要的珍贵的,比如书本的知识,比如友人的记忆,比如组成我人格的事件。
这百年来其余的回忆则大多是交易品,被我无偿赠送给信仰浮黎的焚化工、忆者,换来她们燃烧我一些痛苦的记忆。这位便是其中之一。
她也不恼,左手的掌心竖起点点火焰,焚化灼烧着堆积的灰色忆质,另一只轻点着抽离出的记忆片段,惋叹着:“无用却闪耀的垃圾啊......这么容易就满足了吗?真是可怜。”
那一团游离的流质如若海鳗那般淌回身边,温驯地勾缠上我的手腕。抚摸着这段如清水般柔和的记忆,五脏六腑的痛楚都似乎减轻了不少。
“留着吧。”
她怜悯地吐字:“现在的你应该不害怕成为疯子了。”
是啊。是啊。
将死之人,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?
摄魂夺魄的食人花眸中读懂了我的意思,她状似同情地抿起嘴角,眼眸泛起潋滟的水光,倏然又吃吃地笑起来,自顾自得,歌咏那般,“可惜、可惜,又要少了一位老主顾——这样吧,死前给我发一份邀请函怎么样?我来给你安排一场盛大空前的焰火,就以......这百年来的痛苦为燃料如何?”
幽蓝透明的忆质随着她愈发兴奋的神情旋转起来,恍若漫天的流星划过深色穹苍,留下丝带状的斑驳印迹。
我欣赏着这广阔的盛景。
“焰火就不必了。痛苦我能全部给你,如果你可以一次性拿走的话。”
她板平了嘴角,嘟囔道:“无趣、真是无趣——算了,我还是从你以前的记忆里挑一段吧。”
“好。”
环绕在摊开的重重螺旋中,我冲她略略摆手,“拿走吧。”
耳边有谁在哼着催眠曲,情人那般的低语,头顶旋转的忆质变得透明,泛着拂晓的白光。
当神思回归躯壳之际,睁眼也是一片刺眼的白,一目了然的明亮。
是清晨。
是新的一天。
是尚未死去的一天。
.
茨冈尼亚的白日多数烫得惊人,但很偶尔的,灼烈的太阳会被稀薄的云层遮蔽,留下氤氲朦胧的凉意。
许是因为与焚化工的交易让我感到些许抽离与空虚,我在这一日起床后便外出放风,独自一人这里走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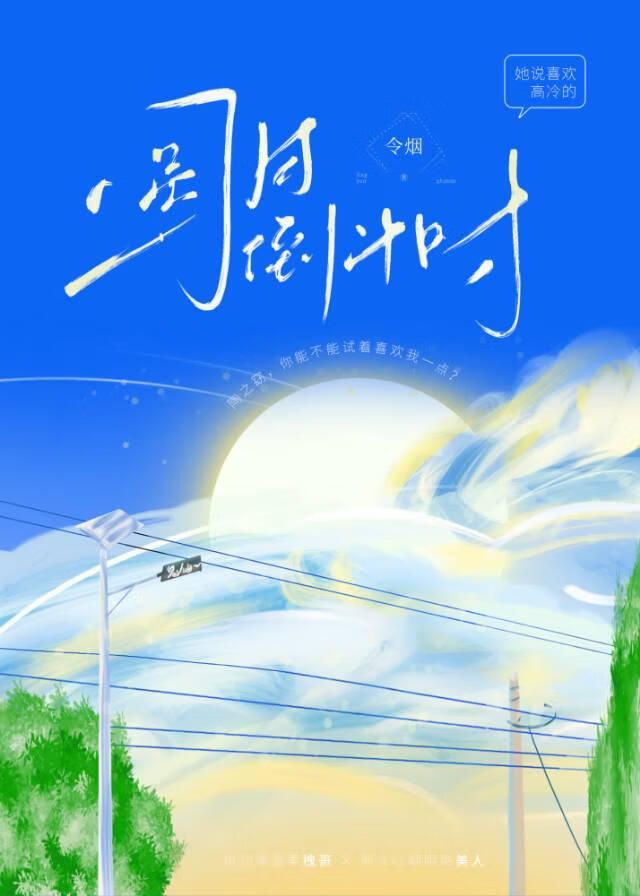



![怪物饲养员[无限]](http://cdij.cn/images/1611/438e2f8cc1171cbdfc48f2edb572375f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