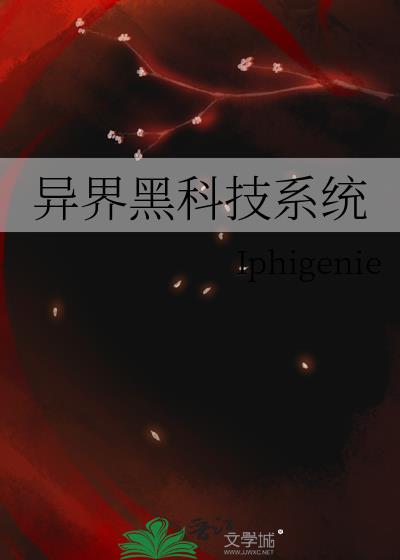雕弦暮偶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雾添花cdij.cn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褐色痕迹,显得很是头疼:“凶器消失了。按照寻常想法,要么丢掉凶器,要么擦干血迹藏于怀中。一直带到久辉阁,是一种意有所指的暗示栽赃,也有可能,这里能更快处理掉凶器,凶手有恃无恐,仍旧能施施然上楼继续赴宴。”
容渡大骇:“那是……?”
宣榕神色有点冷:“是冰,有人做了冰刀。从锋利程度看,应当有模具。”
事情进展到此,已不是简单的杀人案了。
摆明了有人设局,一杀人,二栽赃,三,激怒太子殿下。
不知最后会牵扯到多少人。又或者,到哪一层为止,抛个替罪羊出来。
容渡举棋不定:“那……那现在是……?”
宣榕没亲眼瞧见如舒公的尸身,但听到伤情描述,已是胸口发闷。
她握拳按胸,沉吟片刻:“这事我管不了。监律司也管不了。去给娘亲送句口信吧,我先回府了。同时,速去其余几
个嫌犯府上和亲邻处搜索,模具或许还在。哦对了,还有一事,所有嫌犯扣押和审讯,小心有人下杀手。”
容渡领命,仍旧像兄长一样,将“弟弟”领出,刚想唤个同僚顺带送她回府,便听清朗一声:“阿松。”
宣榕:“……”
她迟疑着转身,果见一个小少年负手而立,明黄滚蟒华贵骄矜,四面八方火光闪烁,他面色沉凝:“我就知道是你!!!”
他痛心疾首:“果然是你!!!”
宣榕:“…………”
谢旻未点破她身份,甚至挥手让随从退后,缓缓道:“你不是说,你不会插手此事吗?”
宣榕轻轻道:“阿旻,我说的是,他若真杀人,我必不包庇。”
谢旻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,眼眶止不住泛红:“姐,你知道,我说的不是这个。我只是在恼,你又选择保他,不站我这边。上次也是,这次也是。帮理不帮亲也不是这么用的。”
“……”哪跟哪啊,宣榕犹疑道,“耶律?不是。或者说,不全是。”
她尚未从风寒痊愈,脸色尚带苍白,唇瓣也没多少血色,一指那边被小心挪出保存的湿血炭,没被谢旻激烈的情绪感染,依旧平和:“这处痕迹你看到了,是疑点。而且还有一点,你不是喜欢喊御林军的人,今日,谁把御林军喊来的,谁让人弯弓搭箭的?”
话音刚落,谢旻眯了眯眼:“萧……?”
他本也是权谋里浸泡长大的,意识到不对劲,含糊地一掠而过,转而痛斥:“可你也不能大病初愈,手掌又被划伤的大半夜,还千里迢迢跑过来啊?!要睡不要睡了!那伤口我一看就疼,你从小到大,什么时候流过这么多血?!”
宣榕:“……”
宣榕低头看向手掌伤口。
纱布上渗出了淡淡的红。
谢旻更为大惊失色:“又崩了?!藏月这么锋?怪不得一直锁起来。”
他上前一把抓住宣榕手腕,左右端详,下了断定:“你这手得残小半月。快回去吧!别再插手了!!!若你之前没搭理过耶律尧,我不信今天的替罪羔羊会是他!摆明了有人借机除他!当初你就不该给他出头。”
本以为宣榕会辩驳,没想到,她沉默着点了点头。
有时候权势无罪。
但奈何人心善猜忌,无罪变有罪。
宣榕定定地看着掌心,不得不承认,父亲是对的。
她还无法掌握这把锋利的刀。
谢旻一看她居然赞同,更惊疑了:“姐???”
宣榕拢袖,袖里,是习惯随身携带的藏月。她左思右想,还是缓步上楼:“我去和耶律说几句话。证据已有人去查了,阿旻,你先预排一下这事会如何收场。”
谢旻脸色阴晴不定,怒极反笑:“收场?若真是他,我要让他收不了场。萧妃刚生的小儿给了他底气是吧,敢算计到我头上——阿渡,你跟着表姐上去。”
五楼视野宽阔,厅堂里杯盏
狼藉(),好端端一场晚宴?()_[((),以官兵拘人结束。
刚走上去,就能瞧到耶律尧靠坐廊柱,修长的手摩挲着一只白玉杯。他一挑眼帘,盯着着宣榕自然下垂的右袖袖袍,半晌,笑道:“郡主可真是慈悲心善,又来帮我了?”
宣榕在他身侧站定,垂眸,轻声道:“你是早就猜出凶手是谁了吗?”
耶律尧缓缓道:“不,我亲眼看到了。”
宣榕问他:“那你方才怎么不说?”
耶律尧冷笑道:“我没给够谢旻暗示吗?是他榆木脑袋绕不过来!而且,我就算说了,谁会信?不过打草惊蛇,赶着催促他们去销毁证据——如果证据还有的话。”
宣榕苦笑了声:“所以你在把这事闹大。”
闹得越大越好,最好惊动帝王,能听他当面陈述。
耶律尧不置可否:“这不没闹大么。”
宣榕默然:“你……今日可能还得去昭狱一趟。不过没事,我令人


![[崩铁]救世主的退休生活](http://cdij.cn/images/1503/8a2f60f4cf86522711d321ca413f5a17.jpg)
![帝国第一王子[西幻]](http://cdij.cn/images/629/0284c5845e22f834ba1172e524d9a09a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