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狋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雾添花cdij.cn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东都洛阳一行,澧王过两日便收到了消息,他当即到绛王府中走了一趟。刚进府门,就见正堂硕大的白幡,扣一方阴阳鱼,府中下人躲在幡后侍弄着火盆,正将一本本道经投入其中。
李悟身披狐裘立在堂前,听见脚步,转过身:“皇兄有何事找我?”
纸页在他身前被火舌卷成飞灰,一一飘散,赤狐皮毛如同与大火融在一起,便是如此颜色,也掩不去半分疲倦与哀痛。澧王先闻见焦味,厌恶地皱眉,又听他嗓子有些哑重,这才缓了脸色。
“听闻你死了师父?要去洛阳?”
李悟叹了口气,面色沉静地说:“正是,邙山上清宫广宁真人,是为我授箓的师长,他此次羽化,我向父皇求了恩典,准我去洛阳,一时也不知几月才回。”
澧王瞥了一眼火盆,抬腿绕过去:“不知几月才回?说得倒轻巧,那太子呢?如今正是你我紧要关头,不趁机压倒那边,你就放心?”
发难需要因由,郭氏一族平日所犯也不过欺男霸女、草菅人命那些事,在朝中乃至皇帝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,唯独趁着吐蕃乱边,如能以贪污国财、甚至欺上专权一罪将太子打痛,才有机会令百官赞同废黜。
澧王在主位大马金刀横坐下来,冷笑:“打蛇七寸,时机正好,我就不信你看不清,是不是因为怕了郭氏?这就想躲,果然跟当年一样是个无胆寮奴!”
李悟一僵,墨色的瞳孔略微发颤,森冷严酷,转瞬间掩饰过去。寮奴、寮奴,盛宠不衰,果然令李恽忘记他也是个洗衣婢所生的孩子,一朝得志,也只有这几日骄狂罢了。
他这头沉默下来,挥袍落座下首,便听澧王灌了一口茶,再道:“不过你此去洛阳,倒也不是全然无益,河南尹秦肃,你可识得?”
秦肃乃两朝老臣,先后任宁、代二州都督,数年前留守洛阳。李悟的声音平静下来,轻轻颔首:“秦府尹么,自是识得。”不仅知晓,还与他交过手,不过那已是旧事,他并不打算说给澧王听。
“秦肃留守东都,而非入长安为官,想来...哼,是为了给太子施恩的机会。”说到这,澧王面色一冷,不过旋即又得意扬眉:“但父皇和太子可都想不到,一年前,秦肃便投靠与我,郭祖贪墨一事,便是他传密信告知,如非这样,要扳倒太子,还不知等到几时。”
幕后人原是秦肃么?依过往了解,此人外宽内忌,心狠手辣,倒也相符。李悟闻此言,静了静,只端起茶等他下文。
“秦肃欲将长女嫁我,我已同意,不过,如今宗室大多依附太子,我不欲令其余人知此事,因此,我提了京兆府官媒去洛阳,为我迎回秦氏女。”
李悟手一颤,茶杯中滚烫的水几乎溅出来,一瞬间,他疑心是自己太过挂念,否则怎会从澧王口中听闻这二字。他将茶盏盖上,强压着面色,貌似随意地问:“长安官媒?”
“正是,你此去替我盯着些,莫要令此事出差错,影响我与秦肃之间的约定。”
李悟面色如常,心下却是五味杂陈,原以为朝局虽乱,只需疏远一时,便不会影响到她,孰料有些事竟偶然至此。他唯恐心事泄露分毫,于是低头默默饮茶,片刻后,待心绪平静下来,才道:“官媒年少,又刚刚上任,只怕秦肃以为受了轻视,此去洛阳,不如令我主行此事,官媒陪侍也就罢了,如此虽不合常例,礼数却足够,想来秦肃不会误解二哥的意思。”
“六弟此言甚是有理,那”澧王眼神一亮,将脸凑近,隔着如烟似雾的水汽,越发如同捕食豺狼:“这件事就拜托六弟了,莫要令我失望才好。”
冬日昼短夜长,很快天色将暗。澧王带着卫率们匆匆而去,嘈杂的脚步声消失在廊下。李悟走到窗侧,推开半扇窗,望见院中枯败的花萼,覆雪如泥,原来新春早已远去了。
晚些时候,寒风刮过,掀起一阵凄厉的寒意,正堂支起的窗棂吱哑滑下来,仆从吓了一激灵,正要再去支,被管事经过一掌拍在脸上:“糊涂东西!没看天吗,这都要入夜了,支什么窗子!”
那边压低了声音继续训斥,隐约传过来,一墙之隔,婢女们低头鱼贯进入堂内,点起烛火,呼吸亦不敢大声。
李悟坐在桌边似是凝思,待罩上纸罩,橙黄透过纸面幽幽映着,在脸上割开一道鬼魅般的阴影。
有人格外壮了胆子,上前一步,躬身问:“王爷...要传膳吗?”
他偏过头,烛光正照亮脸额,因眉骨深高,一片昏黑压暗,星点火光似在眼底跃动。
“传吧。”
婢女们心惊胆战地应下。李悟想起什么似的,偏头交待把公孙先生叫来。
晚膳经厨娘、仆役,再由她们一道道呈上来,试毒人揭了盖子,每样一些尝过,待管事巡完前院,嘱咐后院都关了窗,卧房点上地暖,步履匆匆地过来,这会儿才开始用饭。
菜大略有些冷了,鱼羹舀在碗中递上来,李悟喝了一口,放下,不再动它。
“我出府这段日子,你跟着,到洛阳安顿诸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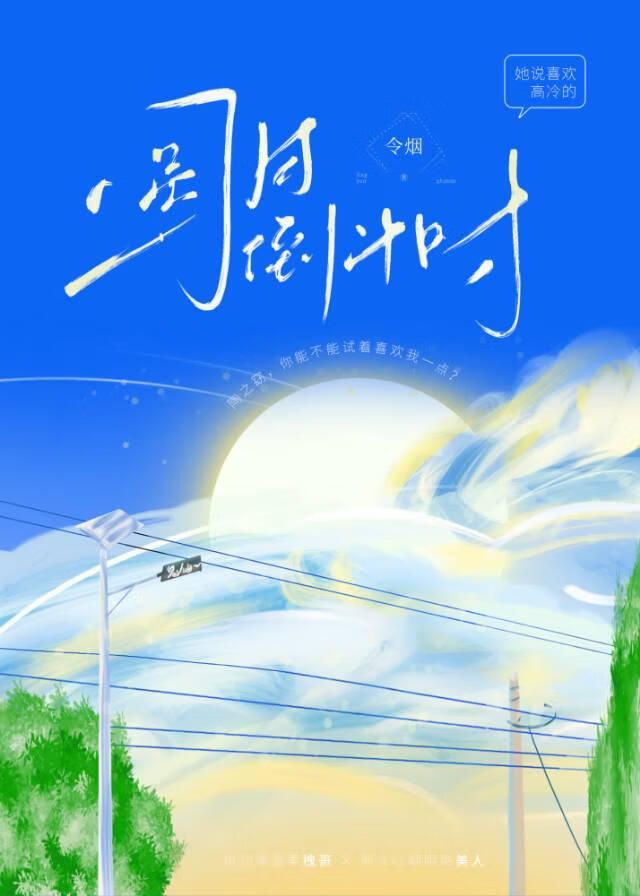



![怪物饲养员[无限]](http://cdij.cn/images/1611/438e2f8cc1171cbdfc48f2edb572375f.jpg)